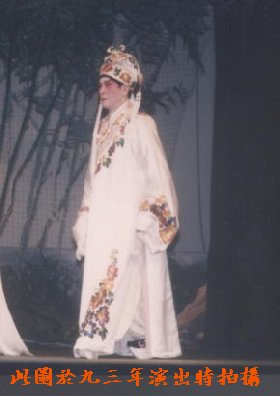| ���G |
�����ܧ֡A�S���A�H�n���u���b�V�e�����I |
| �L�G |
�G���譱����S�O�A���ʷP�C |
| ���G |
�A���S���ѦҨ�L�@�ءH |
| �L�G |
�{�b���ܦh�ܼ@���`���o��k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W����쨫�ɡA�s���U |
|
�����e�]���ʫ��U���L���Y���C |
| ���G |
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[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O�H |
| �L�G |
�]���i��A�[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n���G�ӧO�l�����C |
| ���G |
���u�ݤ@���A�]�u�O�ݤ��z���C |
| �L�G |
��r�A�u�ݤ@���A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ѡA�]���n���U�@���o�i�A |
|
���DzӸ`�|�����F�C�s�Ƥ@�����M�t�X�A�n�ݺt�o�h�`�H���F |
|
�h�`�H������@�ˡA�b�G�C�ӤH��ݱo�h�֡H���M�A�ڭ̰��t |
|
�����h�s�Ƥ@�Ӻt�X�A�W�A�Ʊ���[���`�@�I�A�p�G���� |
|
��A�̲`���ܡA�Z�D���l�]�Q�A�̬ݲM�H |
| ���G |
�ڭ̥��ܦp�����`�A���L�A���ɭԦb�e�Ƭݤ��쪺�A�b��Ƥ� |
|
�Ӭݨ���I |
|
|
| �L�G |
��ť��q�x�[���Q�ɻ��s�B�b�����j�U���^�x�i�ӮɡA���� |
|
�����ʧ@���ѺC�ӧ֡A���T�ݭn�o�˥h���F�J�檺�߱��C |
|
|
|
|
| ���G |
���u���X�v���q���i�H�u�ǡA��֤@�q�p���]�i�H�A�]���� |
|
���e�C |
| �L�G |
�o�ǬO���мw�P�_�j��s�A�ڨS���ѥ[�N���C |
| ���G |
�ڭˤ�ı�o�o�q���Ӫ��A�uı�o�q���۱o�Ӱ����A���L���C�� |
|
���A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o�i�C |
| �L�G |
�i��O�O綫���D�C |
| ���G |
�N�ۤ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D�A��ѥ~�v��y�����K�K..�C |
| �L�G |
�O���_���ۤv�۪��A�L�H�N�r�I |
| ���G |
�۱o�Ӱ��F�A�ӥB�o����ۡu���n
(�h�n)�v����H |
| �L�G |
�w�g�d�LŪ���A�O���ӳo�˪��Ať���o�H�e�t�o���ɡA綫�f�S |
|
�o�˰��A���p�G����C綫�f�A�S�Ȧo���ﳡ���ӧC�A����o |
|
�n�A�G���E�N�F����A�l��N�����F�C |
| ���G |
������b�u�ӥx�۷|�v���S�S���o�ӷPı�H |
| �L�G |
��A�o�O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ըS�����C |
| ���G |
���|�y�ۥѪO�u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X�x�K�K�v�P�S��۪k���P�A�O�_ |
|
�i�H�N��A�S�O�֥h�M�w�۪��Фl�H |
| �L�G |
�ۥѪO�O�i�H�諸�A�o�X�y�Фl�A��Z�O���мw�A�_�j��ӥ� |
|
���ۤv�@�L�ק�A�̫��n�P���֤譱��s�p��Ũ���B�t�X�C |
| ���G |
����ı�o�s�۪k���ίS��nť�A�p�G�i�H�諸�A�U���t�X�ɡA |
|
�i�_�A��H |
| �L�G |
�ۥѪO�O��l���T�w�A���Фl�譱�]�n�ƥ��w�ƪ��C |
|
|
|
|
| ���G |
�A�O�̬ƻ�c��u�篬�v�����ѬO�q�L���H��L�@�ئ��S���o |
|
�ӳB�z��k�H |
| �L�G |
��L�@�إ禳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O�]���Ӭ��ѡC�n���t�@�B�V |
|
�@�B�ʼ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A�^�x�^�a�ɥ�s�H�ߡu�A������B |
|
�ڦa�C�C�ɡv�A�J�M�^�h�ɧ����A�W���ɧ����]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C |
| ���G |
����L�@�ئ��S���s�B���o���H |
| �L�G |
�S���C�ӱ��z�A�ڷQ�L�̥hŪ�ѡA�����ӬO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A�@�� |
|
�k�l���M�O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^�x�w�˧ꦨ�k�l�A�`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A�� |
|
���W�w�n�Ե۰��A�ڦw�Ʀo�����W�ӥu�O���W�A
���� |
|
�o�u�O�˭Ӽˤl�A���קK�P���ͤH��͡A�~�^�^�W�����}�A�� |
|
���o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C |
| ���G |
�A���w�ƬO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ʮ�άO��L�H |
| �L�G |
�^�x�ڥ��O�����o�M�����A�ҥH�o�W���e���ӡu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 |
|
�@�A���ܡu���氨�j���A���n�~��ڧr�A�A�n��着�ڧr�I�v�A |
|
�o�o�����ʧ@�P�@�뤣�P�A�]�o�P����ä��Ѥ͡C���L�A�o�� |
|
�p�ʧ@�A�[�����ɭԫܮe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ҥH���A�[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h |
|
�֬O�ӧO���P���C |